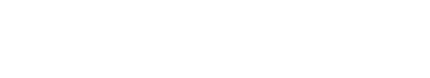“金罗店,银南翔,铜江湾,铁大场,教化嘉定食娄塘,武举出在徐家行。”这是小时候常听到的民谣。其中,“银南翔”指的是南翔过去主产棉花,到了收获时节,到处银白色一片。
嘉定种植棉花由来已久。明代中叶,地处长江口的嘉定,因海岸线向外延伸,地势凸高,自然环境变化,导致不宜种稻,而宜植棉。当时境内农田作物的分布是,十亩田中九亩为棉、一亩为稻。随着时间推移,嘉定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。笔者今年87岁,记得小时候,轧花行、弹花店、纱厂、毛巾厂在嘉定星罗棋布。

从棉花到纺织品的成品,其第一道工序就是轧花——把花衣和花核从原棉中分离出来。地方志记载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嘉定就已有“同丰泰”“仁德丰”“合丰昌”等大大小小六七家轧花行。东门外的仁德丰花行离我家最近,加上我曾与它有过一段不解之缘,因此对它有些了解。
仁德丰花行的厂房在东门外嘉罗公路上,一排四间平房是加工车间,另一排三间平房为库房。由于都靠近练祁河北岸,加工车间和库房都设有水桥,作为运送原料及成品的码头。与库房隔街相望的,是花行老板郁孝廉的住房。它其实位于东大街尽头处,坐北朝南,为两开间三进的两层楼房。

▲上世纪七十年代 沪郊棉花收购场面 陈启宇摄
仁德丰花行在当时,算得上是一家现代化的工厂。因为主要设备是钢铁制造的,且由电力驱动,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轧花行是以子棉为原料,通过轧花机将棉花纤维从子棉中剥离出来,得到皮棉和棉籽。皮棉进一步加工后,在纱厂里纺成棉纱,从而织成毛巾或布匹。棉籽则可加工成棉籽油,又称“花核油”。棉籽渣在当时只能用作肥料,如今还是各种菇类的上好培养基原料。可以说,棉花确实浑身都是宝。
1950年我初中辍学期间,曾在仁德丰花行干过几个月的计件工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导花,即其他人用小车把一箩筐一箩筐的棉花送到机器旁,我只要将棉花均匀地、不间断地丢入开着的机器就行了。每丢完一箩筐棉花,就会得到一根竹筹子,每周花行会根据竹筹数结算一次工资。我对花行的粗浅了解,主要靠这一段短暂的经历。

1953年我复学,毕业后考入嘉定县中学,岂料高中同班同学郁元通,就是仁德丰花行郁老板的儿子。我和郁元通,以及另外两个家住东大街的同学,曾组成过一个学习小组,每周都有三四个晚上一起学习。我们通常都会选择郁元通家学习,因为他家房间宽敞,晚上灯火通明。期间我了解到,郁家总共四人,即郁元通、他姐姐以及父母。高中毕业后,郁元通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,我则考取了南京工学院,从此各奔南北,再也没有过联系。
只听说,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,私营花行也随之退出市场,仁德丰花行几经周折,改名为南翔轧花厂,最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,棉田面积大幅度减少而停产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,嘉定老城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,东门外大街已难觅仁德丰踪影。如今,这里已成了紫藤串串、树木繁盛、鸟语花香的绿地。

作者: 杨培怡
编辑: 沈悦